|
你明早五点在楼下等我,陪我跑步。她说。
我起不来啊,再说早晨也冷,会感冒的。我说。
不行,她强硬起来,你对我怎么这么不好,是我重要还是感冒重要?
你重要!我起。
这是我们昨晚的一段对话。 上眼皮沉重得只掀起一道缝,我摸索着爬下床,套上衣服,看了一眼表,四点四十。我拎着一系列物品去洗漱,所有的声控灯被我一声断喝懒散地亮起来,水龙头欢畅地流淌,一切完毕,我再看一眼表,四点五十。我必须得提前,她说这是男人的风度。我踏出楼门。
太阳还未起床,我站在楼下望着她昏暗的窗,受冻了一夜的冷风终于找到了取暖的去处,它们争夺着窜进我的袖筒、裤管,再向内,在我两周没洗过澡的皮肤上寻觅温度最高的一块。在它们面前,我变成裸体。
十五分钟过去了,我凝望她的窗口,无光,我躲在一个墙角,紧了紧衣服,出来时没有带电话,我以为这样的早晨电话是会被冻得失灵的。我吐出白雾,把手放在雾中取暖,可是雾已经凉了。前天下了雪,昨天化掉一些,今天又冻得僵硬、光亮,映着天空,整个世界都显得格外透明,坚强。四周无人,远处的体育场应该有许多人,其中有人挥汗若雨,有人期盼太阳。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在墙角抖成一团,取罢暖的风开始从我的领口幸福地姗姗而出,然后又有一些初到的风慌忙地挤进来,与我交换体温。我成了一扇无私的天然暖气,从自然的角度看我好似如此伟大啊,可是在我渺小又卑微的心灵里却是满怀怨气。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变成了冰人,我感到四周暖风吹拂,连这风也会嫌弃我不够温暖。我的肌肤不再是温暖的施舍者。望向窗口,充满绝望。我像一个在雪地里玩耍多时的孩子,对寒冷麻木,现在就算有人用刀捅进我的肚子,我可能还要对凶手善意地说,瞧,你的手流血了。
太阳升起,我平生首次如此成功地观摩了日出的壮景,不知多久以后,阳光通通洒在我的身上,像一个手电筒照过来一样,充满光彩却没有温度。路上开始有了一些匆匆赶往课堂的苦命学生,他们诧异地看到一个眼角与鼻孔挂着冰渣,表情凝固,双手深深插进衣兜,双腿时有战抖的风中男人,此场面在某种层面上充满无限张力。
我想我是应该回去了,我在此树立的价值已经随着时间的前进势必归零。我转身,这时一个声音喊住我,她问,你在这站着干什么?我茫然回头,她表情比我更惊讶,我说,没事,就是想找你一起跑跑步,可惜现在不行了。她一拍头,如梦初醒,说,忘了,忘了,全忘了!她过来双手托住我的脸说,冷吗?我感觉到了她手上的温差,但却不清楚那是冷?是暖?我说,刚才冷,现在不了。她身后走来一个女同学拽她赶紧去上课,她匆匆向我挥手,说,明早一定起来,等我!我说,好的,等你!
一些人走进热气腾腾的食堂,那里有稀稀的粥和白白的馒头,我没去,径直回了寝室,睡着了就不饿了。我兜里很干净,没钱了。我走进寝室,感到春天与冬天是如此逼近,只有一门之遥。脱掉衣服,爬上床,常温下的被子此时变的暖意昂然。眼皮落幕,合得很塌实,在困意袭来的间隙,我极力思考着还有谁能够借我一些钱,才能够不让中午时我的女友挨饿。我已欺骗父母几次,构思了许多抽象的理由向他们要钱,如今我已不忍心再去污染他们对我那源源不绝的高尚的爱。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躺在我们吃力营造出来的“家”里,我花掉了一年的学费,租了这间一室一厅。这是她的愿望,她用我的学费把这个家打扮得像新婚男女的家,应有尽有,幸福祥和。我看着她高兴,我也高兴。她经常去逛街,把购置家具当成一份工作。我们几乎总要出去吃东西,价格不菲,这使我精心挑选的炊具丧失作用。她的食欲与购物欲都很强大,让我单薄的学费难以抵挡,我终于看到了钱是这样的不筋花,好像一块巨大的面包被掰碎后不知不觉就消失在口中,最后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胃。几千块在不知不觉间就化为乌有,我无法回想起它们究竟变成了何种存在形式,我只记得她很快乐,而那时的我很麻木,看着她开心,我想象不出几步之后的路况。
学费没了,房租交不起,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常规的生活方式中。我每月几百块的生活费再次难以支撑,经常引发我对明日复明日的感叹。我们曾在没有钱去食堂的中午绕到学校后面那条只有大型机动车飞驰没有行人的马路上,扬尘厉害,我们边走边笑,吃得一嘴灰黑。我说,我们这种三天乐的花法太刺激了,现在我们连买三个包子的钱都没有。她说,一分都没有了?我说,不,还有五毛。她开心地指着远处的街边说,那我们去买一袋爆米花吧!我说,好!从来都是我先对明日的食物忧愁起来,因为从来都是我先感到饥饿。
女友喜欢穿戴,为什么女人的攀比心会这么强,总想与人在外表上争个高下,看到漂亮的衣服她会跟我要,看到昂贵的首饰她也会跟我要,看到新品手机她会跟我要,看到时尚跑车她也会跟我要,甚至看到高高飞翔的民航飞机她都会跟我要。她看到我一次比一次更吃惊地说出“买不起”说我没骨气,不像一个男人,说,即使目前买不起也应该先答应下来,作为努力的目标。这时,她一直是一个爱花钱又没有钱而且也没有一个有钱老公的女人,最多只会情急之下单纯地说我没骨气,不够男人。
一年之后,我们的生活默默地翻个半个筋斗,这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女友与我的见面时间已由早期的一天中的十二个小时更改为十二天中的一小时。女友变成了富婆,挥金如土,几千块的衣裤、鞋子,几百块的钱包是她很随便的消费,她不再需要我的生活费对她的支撑,我宽松许多。她总让我猜她新买的某件东西的价格,我不猜,说猜不到。她兴奋地向我报出天价,然后眉开眼笑地跟我介绍其中妙处。我问她哪里会有这么多钱?她说是*本事挣的。我说你是否去****了?她急了,臭骂我一顿,哭着跑回寝室。她经常出入一些星级酒店或高档娱乐场所,接触了许多她认为有身份的达官贵人,这是她在跟我炫耀时不慎说出来的。我曾劝她不要去了,这不是正路,我说,你陪人家吃吃饭喝喝酒,人家给你一些钱,这是出卖色相,再说万一遇到流氓,后果就严重了。她不听,因为她跟我要钱时我没有,我不劝了,因为我在金钱方面说话很无力。
我喜欢我的女友,十分喜欢,不会放弃她!
暑假回到家里,父母又买回大堆的鱼呀肉呀,这是他们平时不舍得吃的。这几年虽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他们还是过得很小心,几毛钱、几毛钱地算计着花,不愿意丢掉补了多次的破鞋子,过性的线衣也不忍心扔掉,剪成一块块的做抹布。两位劳碌了半辈子的老人再也干不动了,只有省,多省一分就多攒一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如何挥霍掉他们的血汗,不能告诉他们女友身上任何一件衣物或饰品的价格,会吓倒他们的。
我去了女友家,这是一片棚户区,大多数居民没有稳定工作,上了年纪的人穿着几年前的衣服,搬个方凳坐在家门口观赏天空与太阳,或是来回行走与邻居聊闲。年轻的一代衣衫时尚新艳,干净利落地出门打的去向多彩的消费场所,他们活得潇洒体面,不像他们的父母。女友家住在这里其中的一间地房里,光线昏暗,冬季难熬。她的母亲更加辛劳,拼了半辈子却还要马不停蹄,最大的愿望是能住得上楼房,而从经济方面看,还是要拼上若干个年头的。
我说,我们还不是享受的时候,看你的父母还在早出晚归,很累。
她说,所以我要赚钱,给他们买好东西。
我说,你走的不是正路,况且你这一身上下加起来已经够他们吃用上一年了,你不如省下钱让他们休息上一年,人要是上了年纪身体比穿戴更最要啊!
她说,你就会说我,你要是能挣钱我用这样吗?谁不想每天呆在家里,我才二十岁,别的女人有的我差啥?
我说,你的确不差啥,就差一个有钱的老公!
我俩一同去逛街,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走在她的身后像一个跟屁虫,为她提着刚买到的大包小裹,而她一向两手空空。走在高档的大商场内,她五光十色,对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国际品牌指指点点,这个两年前还对我脚下穿的一双“李宁”鞋感到昂贵的女人如今已奥妙地衍变成一个上层人士,而我则成功地变成了一个吃土耕田的农民,与这个若大的城市格格不入。我像一个贵夫人身边的脚夫,永远站在与舞台光柱一步之遥的黑暗里,无人观望。她让我装出派头,哪怕兜里没钱。我说,我无须别人瞧得起我,只要我瞧得起自己,何况也不一定非得是有钱人才能受人高看,她瞥我一眼,朝前走了。
我们一起吃过很多次高档的饭,事毕,她把钱夹塞过来让我埋单,说这样我才有面子。我大喊,算帐!服务生看着我愣住,我又重复,服务生依然迷惑地看着我。我说,埋单!服务生恍然大悟。女友说,这里不是食堂,也不是小摊店,这是高档酒店,是上层人来的地方。我不懂,站在高档酒店里的服务生也会层次彪升,看我反而不入流。我清楚地发现出入这酒店里的男女大多年近中老,我说,看,我们确实不是享受的时候。
夕阳斜映着校园,无数的人头影影绰绰,我拍拍干瘪的口袋,沉着脑袋走进人群,我是一个男人,凡凡的男人,来去无声。 我喜欢我的女友,但,我没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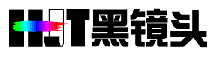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7/8/17 13:40:3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7/8/17 13:40:31 [只看该作者]
